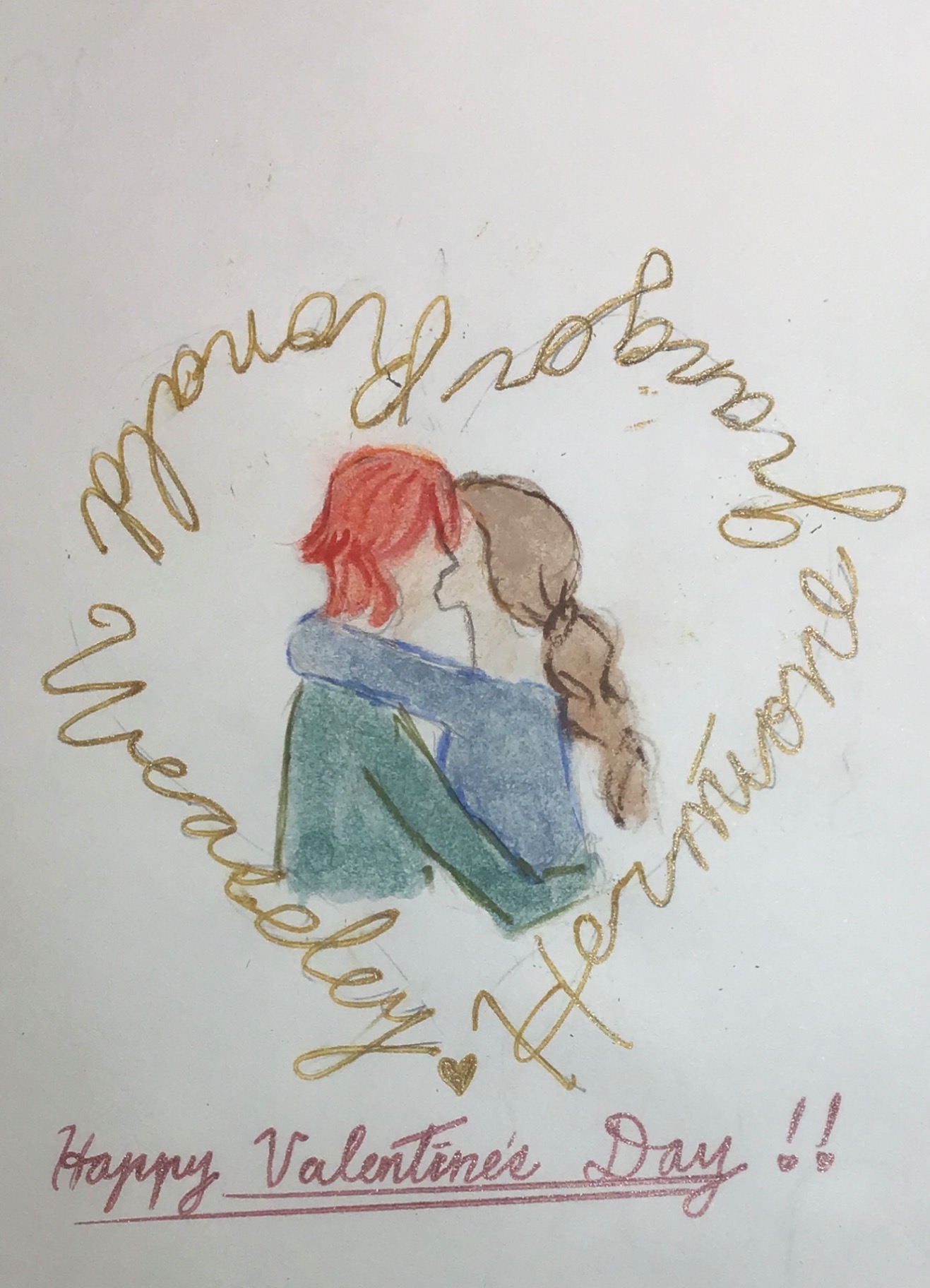那些沾枕即眠的人是怎麼做到的?
肚子空落落的,但也不怎麼想吃東西。
從那時……從他發生那件事後一直到現在,她就是提不起勁。
今天她又哭了。
這是第幾次?
秋從床上坐起來吸了吸鼻子,儘可能小聲地披上外套。丑時的走廊靜謐得連壁畫裡的人們都睡著了。
沒有什麼是永遠不變的。
這是她今年重新認識到的事。
而她恨透了這句話。
秋不是不懂朋友們說的「要走出來」。
她也知道大家都在往前走,如常上課、學習、練球,就這樣追趕著時間跑過。
可是——
西追的臉又浮現在眼前。
如果——只是如果——
自己也不想走出來呢?
生活中那些絢爛的時刻,幾乎都跟某人有關。要把他甩在後頭任由時間覆蓋?
……
明明她才是那個還留在原地的人。
你為什麼就這麼死了?
她沒有勇氣把這句話說出口,但它從暑假開始就一直卡在喉嚨裡。
即使說了也沒有用,因為他聽不到。
永遠聽不到了。
我該怎麼辦?
我又該拿你怎麼辦?
約定好要完成的清單、一貫的溫柔、顯得真誠的笨拙、體貼紳士的舉動,和那張總對著她微笑的臉。
沉甸甸的。
不知道怎麼著,自己開始往上走,一層接著一層。
回過神來打開門,她愣了一下——塔上已經有人了。
那人正坐在地上,裙擺隨意地散開,淺金色的頭髮在月下閃爍。
露娜·羅古德抬起頭,像是早料到有人會來,對著她揮手。
「你好。」露娜的聲音輕得像一縷霧。
「露娜?你在這裡做什麼?」她挑挑揀揀,從記憶裡找到這個名字。
「我醒著,天空也是。」
「噢。」她不知道自己還能說什麼。
露娜沒有繼續說下去,或者起身,只是抬頭望著夜色。
張秋不知道該不該走近——但既然已經來到這裡,又沒有力氣轉身離開,她只好慢慢地走到女孩身邊坐下,把下巴抵在膝上。
兩個人就那樣沉默地坐著。
「嘿,你有什麼……助眠的方法嗎?」明知道問了也可能沒用,但還是問了。
露娜眨眨眼。「有啊。」
她挑眉,不抱希望。
「那需要很慢、很慢地眨眼。」
「像貓相信你、不會跑開的速度。」
「為什麼是貓?」
「因為貓不會替別人失眠。」她很自然地回答,好像這件事天經地義。
「它們睡著的時候,整個世界就應該要跟著入睡。貓很驕傲的。」
露娜突然抬手,指尖輕碰自己的眼皮。「像這樣。」她眨了一下,非常、非常慢。
秋有點尷尬,但出於禮貌也開始模仿。
兩個不熟的人並肩坐著,慢慢地眨眼。
一下,又再一下。
只是坐著。只是呼吸。
只是和另一個也醒著的同類伴著星辰一起慢慢地眨眼。
這樣的畫面聽起來真奇怪──奇怪到有點好笑。於是她忍不住發出一個短促的鼻音,接著輕笑。
露娜側過頭,盯著她看了好一會兒。
像是在確認什麼只有她能看見的東西。
「找一顆你願意相信的星星,然後告訴它:『我現在要睡了,你幫我看著世界一下。』」露娜說得很認真。
「這樣就不用負責所有事情了。」
秋瞥見她的腳趾蜷縮了一下。瘦瘦的腳背迎向一陣陣風,看上去幾乎是半透明的。
她不是第一次看到對方赤腳。
也不是第一次在走廊聽到別人嘀咕議論露娜是個怪胎、不合群,別靠她太近。
她也曾經把這些話當成遠處的紛擾,沒怎麼干涉。
因為生活已經把自己耗盡了,沒有辦法再顧及其他人。
但現在,看著看著,她突然有一種莫名的衝動:想做點什麼、哪怕只是微不足道的。
不是出於義務或憐憫,或許是留下這一晚吧。
她彎下腰,把自己的鞋子拎起來,
「這個給妳。」她把鞋塞到露娜面前。
露娜嘴角上揚,就好像——她一直知道秋終究會這麼做。
「……交換。」
露娜慢慢地、很小心地把腳伸進鞋子裡。
鞋子大了點,但她一點也不介意。
「謝謝你。」她輕輕說。
秋沒有回話。
她只是讓腳指頭探向堅硬的石板,用那一點點支撐站起身。
沒有退縮。
或光腳或穿鞋,女孩們一前一後走下樓。
冷意從足底往上蔓延,卻帶給人一種奇妙的踏實感。
是啊,她真切活著,仍在呼吸,也仍在悲傷。月亮還醒著,天空也是。
睏意悄悄地攀上她的眼皮
「晚安。」她低低地說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