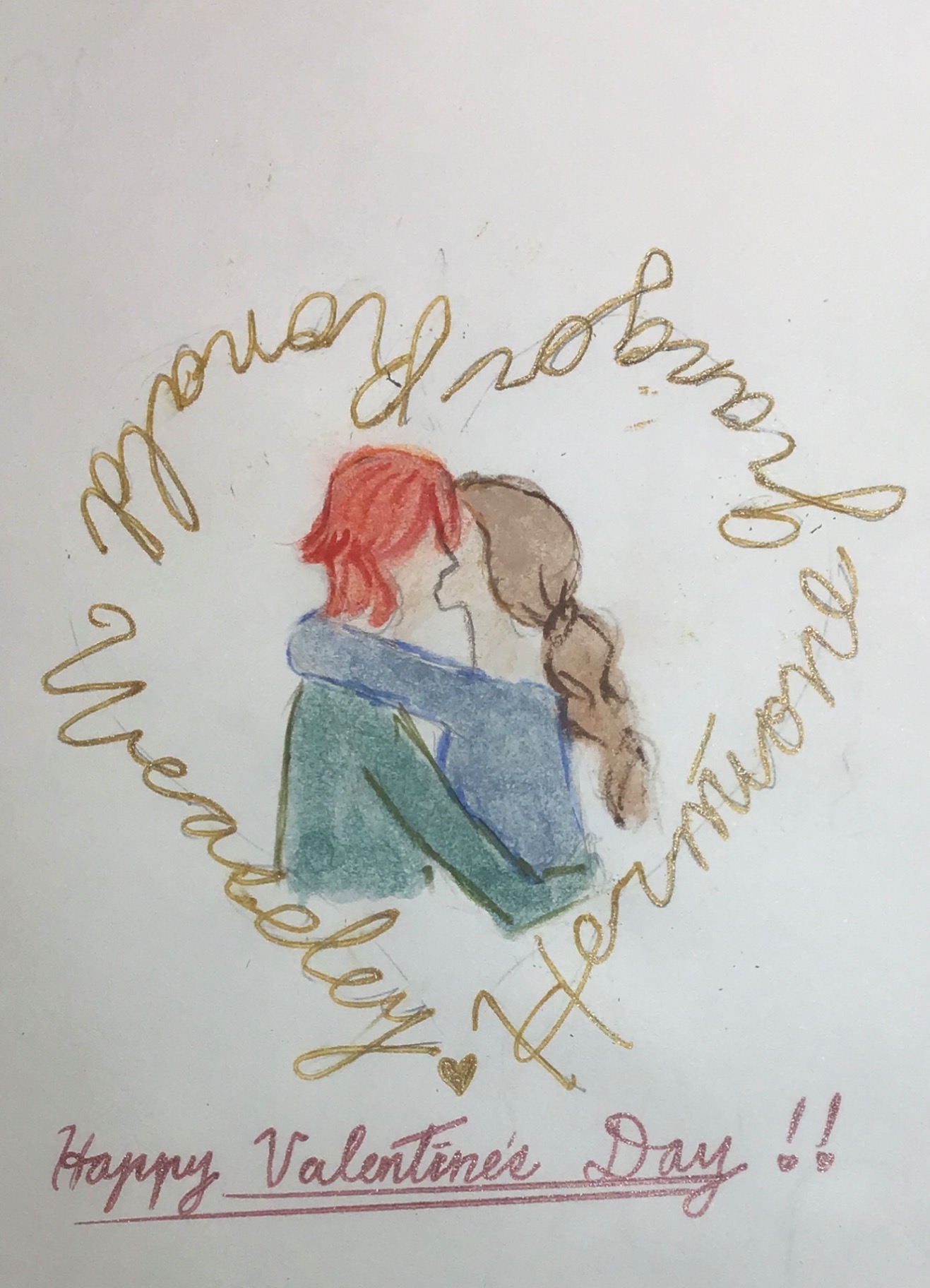第十章 存在的證明
傍晚下課鐘聲響起時,教室外的走廊早已熱鬧起來。學生們三三兩兩地離開,還有人邊走邊回頭繼續著剛才未竟的話題。容安走在隊伍後頭,莉莉和她一道出了教室,與兩名同學短暫交談幾句後便轉身離去。
她走得有點快,像是預料到了什麼。
果然,轉角處,一道熟悉的身影已經靠著牆等著了。詹姆·波特——凌亂的頭髮更亂了些,還有張嘴就來的笑容,正朝她揮手。
「伊凡小姐!」他半鞠躬,語氣誇張,「我正苦惱今天還沒見到妳,沒想到命運就把妳送到我面前。」
「命運要是有眼睛,大概早就瞎了,」莉莉冷冷說。
「那也瞎得可愛極了,不是嗎?」他笑嘻嘻地跟上。
容安站在轉角沒出聲。她不確定自己為什麼停下腳步,只是看著那一幕,腦中浮現了希羅教授在課堂上說的話——
情感是一種強大而原始的魔力。
她從不理解這種力量為什麼會驅使一個人反覆做著相同的事,像詹姆·波特這樣——一次次被拒絕,卻仍每天守在走廊口等著一個冷漠的回應。
若這不是無意義的重複,那究竟是什麼?一種執念?一種愚行?還是那所謂的「喜歡」?
她曾無數次目睹他追著莉莉跑,從未覺得有什麼可看。可不知為何,經過那一堂課後,她腦中那些聽不懂的詞彙、夢裡那個低語的聲音,竟讓她對眼前的場景產生了某種停留。
或許是好奇。又或許,只是因為——那聲嘆息太不像他了。
莉莉的身影很快消失在樓梯口,留下一句「你再跟著我,我就把你變成一隻跳蚤」的警告。
詹姆站在原地,看著她走遠,臉上的笑容沒有馬上退去,只是嘴角彷彿微不可見地往下沉了一線。
然後,他輕輕嘆了一口氣。
不是那種戲謔的聲音,而是真實的、很輕的呼出氣息。
那一瞬,她第一次產生了一個念頭——這個總是熱鬧張揚的人,是不是也有什麼,是她看不懂的?
她走了過去。
「你每天都在等她?」
他顯然沒料到容安會主動跟他攀談,愣了半秒才笑起來:「容安——妳來得正巧,我正打算設一個陷阱,下一次她經過就……呃,當然是為了給她驚喜。」
「她看起來不喜歡驚喜。」
「不,她只是嘴硬,」他眨眨眼,仍是一副嘻皮笑臉,「再說了,我不做這些,她怎麼會記得我呢?」
容安靜靜地看著他,語氣仍然平穩,像是在陳述某種觀察結果:「她會皺眉、罵你、躲你……代表她一直都知道你在那裡。」
她頓了頓,眼神不閃不避,說得像是給出一個總結:「她早就記得你了。只是暫時沒有想要喜歡你而已。」
那句話像一把刀,削去了他所有拿來自嘲的語氣。
詹姆眨了眨眼,像是那幾個字卡在喉頭,嗆了一瞬。他沒有立刻反駁,只是摸了摸後頸,嘴角的笑意像落了水,靜靜褪下去。
「……妳真會說話啊,容安,」他終於開口,笑得有點勉強,「妳總是這麼直接嗎?」
容安沒有說話,詹姆則是摸了摸後頸,有些無措地轉開話題。
「那妳呢?心靈術這種課妳也有興趣?」
「莉莉邀請我旁聽的。」她語氣平淡,「我聽不太懂……尤其是後半段。」
「太抽象了?」他似乎有點好奇。
「不是抽象,是……我知道那些字,但不知道它們代表的情感是什麼。」
他挑眉:「什麼樣的字?」
「比如說,戀愛。」
這回連詹姆都沉默了一下。他大概從沒遇過有人這樣正經又直白地問出這種話。
「啊——這問題太大了。」他笑了出來,語氣像是在故作鎮定,「戀愛嘛,就是……就像想每天見到那個人,想知道她在想什麼,說什麼都會聽得很仔細,即使是罵你……你還是會想再聽一次。」
容安若有所思地點點頭。
她沉思片刻,語氣毫無評價地問:「那她永遠都不會喜歡你的話,你還愛她嗎?」
這句話像是一把直刀,削破他所有用來掩飾的氣氛。
詹姆笑容一滯,半晌說不出話。
容安還是那副無波無瀾的語氣,像是在學術討論般推論著:「教授說,最強大的愛是無私的。那如果你喜歡她,是因為你想被她喜歡,就不是愛吧?那只是……渴望被看見。」
他怔住了。
從沒有人——從沒有人這樣說過。大家總笑他癡情、執著、追求不懈,但沒有人問過他這麼簡單、赤裸的問題。
他突然不知道該怎麼應對,只能撓撓頭:「哇,妳真會問問題。」
容安沒有笑,也沒有追問,只是靜靜看著他,像是在等他誠實地回答。
過了一會兒,詹姆移開視線,語氣有些模糊地說:「我不知道……從一開始,我就習慣讓她注意到我。不鬧點動靜,她根本不會看我一眼。妳說的也許對……我只是想被她看見吧。」
說完,他又笑了,笑得輕浮,卻笑不進眼底:「聽起來挺可悲的,對吧?」
「不可悲,」她像是在描述一種現象似地說,「只是有點急於證明自己的存在。」
這句話比任何評論都來得更真切、更無所遁形。他猛地抬頭看她,眼裡掠過短促的驚訝與不知所措。
容安繼續道:「你做了很多事,只為讓一個人注意你,但你不確定自己喜歡的是她,還是那個被她注視的自己。」
詹姆沒有說話,站在那裡,像是忽然被迫對一面鏡子誠實。
許久,他才深深吸了一口氣,低聲道:「妳這人……講話像刀子,劃得乾淨俐落。」
容安歪了歪頭,不置可否。
他望著她,又補了一句:「跟妳說話挺危險的,誰知道下一句會不會就被剝光自尊。」
這次換容安沉默。
她不明白剛剛說的那些話為什麼會讓他有這種反應——那只是她對某種情緒的觀察,不帶任何感受。可他像是聽懂了什麼很重要的東西。
詹姆彷彿想再說什麼,最終卻只是笑了一下,像怕氣氛再變沉重。他舉起手輕輕對她做了個打趣的敬禮姿勢。
「晚安,容安。」
那笑容依舊是大家熟悉的詹姆·波特,可離開時的背影,像是匆匆想躲開什麼,彷彿在刻意逃避自己剛被觸動的地方。
那天晚上,她再度夢見火焰。
那不是現實世界的火種,而是一種炙熱卻無聲的灼燒,自她內裡某處蠢動著漫延而來。她站在一片昏紅的空間裡,四周是一層層交錯的火牆與符咒結界,氣息沉重,仿佛每吸一口氣,喉嚨都會被煙霧劃傷。
她知道這裡。
這是灼夢堂。
不是因為想起,而是因為身體知道。那裡的每一塊石板、每一道焰紋、每一縷空氣的厚重,都早已烙印進她的骨血。她曾跪在那片石地上,接受過無數次訓誡與壓制。
夢裡,她跪坐在堂中央,周圍站著幾名身穿赤袍的長老,面容模糊卻目光如炬。他們的聲音不帶怒氣,也不含情感,就像年復一年的冷風,穿過山谷,冷冷劃過耳膜。
『情緒,是魔的根源。』
『波動,只會使你墮落為獸。』
『你必須學會平靜,否則——』
話語斷裂,化作煙霧,與火光一同在空中游移不定。容安低著頭,像是在聽,又像是聽不見。忽然間,那些話語變了調,一個更輕盈、斷裂的聲音從火焰深處浮出來,像細絲般滑進她腦海——
『妳說妳已經學會平靜,說妳早就沒有情緒了。』
『可妳不是麻木,只是不動聲色罷了。不是嗎?』
『那些夜晚,那些對話,那聲嘆息……每一絲妳都記得清清楚楚。』
『他們的世界開始動搖妳了,不是嗎?』
『妳在好奇。妳在想,如果妳也能像他們那樣笑、那樣生氣、那樣……被愛,會怎麼樣?』
『那個像風一樣張揚的少年,總是笑著闖進每個場景,把沉默變成笑聲。』
『那個帶著雷聲的眼神,像是隨時會劈開黑夜的人,目光銳利得教人無處可躲。』
『還有那場綿綿不斷的雨,不語,卻滴進妳骨縫,教妳無法忽視。』
『妳以為自己無動於衷,可他們的存在早已在妳心裡留下痕跡。』
『妳不是麻木,只是不願承認而已。』
那聲音既熟悉又陌生,語氣柔和卻帶著輕蔑的洞察力,就像某個與她同體的存在正在打量她心底的每一道裂縫。
她想反駁,但發不出聲音。符咒陣忽然亮起一道紅光,一陣刺痛從胸口蔓延,整個夢境像被火舌撕扯,瞬間崩解。
容安猛地睜開眼,額上沁著冷汗。
她坐起身,望著燭台上未完全熄滅的火光,心跳尚未平復。那夢……太真實了,真實得像是回到了過去的某段時間,而那被封印的東西,彷彿正從縫隙中張望。
這樣的夢境,自開學以來越來越頻繁。起初只是零碎的畫面與模糊的聲音,如今卻有了完整的場景、明確的語句,甚至能感覺到封印本身的痛感。
她曾猶豫是否該寫信給族中的長老回報這些異狀。那是她應該做的。但她遲遲沒有。
她說不出那是為什麼。
只是模糊地知道,自從進入霍格華茲,事情就漸漸不一樣了。
這裡的學生會在走廊裡為一場惡作劇笑到彎腰,也會在課堂上為一個觀點爭得面紅耳赤。有人會毫不掩飾地向心儀的對象示好,即使年年被拒仍不曾退卻;也有人縱使被萬眾注視,仍能不動聲色地做自己,像全世界的目光從不曾成為束縛。
容安不明白他們為什麼能活得那麼坦然,情緒那麼明亮、直接、洶湧,像是不曾學會壓抑這件事。她只能靜靜看著,像看著一場和自己無關的盛宴——繽紛得教人目眩。
這裡,允許情緒存在。
而她,從未真正學過怎麼擁有那些東西。她曾經以為,壓抑就是平靜,無欲就是清明,沒有情緒就是控制。
但她錯了。
封印鬆動,並不是因為她變弱了,而是因為這裡太過強烈地提醒她——她其實從未學會怎麼活著。
發表於
Yian @yianc
3
A.S.Vale @A_S_Vale
1
@yianc
原來是長老們要把她訓練成沒有情感的AI(喂
本來只是懷疑容安是不是亞斯伯格
夢裡,她跪坐在堂中央,周圍站著幾名身穿赤袍的長老,面容模糊卻目光如炬。他們的聲音不帶怒氣,也不含情感,就像年復一年的冷風,穿過山谷,冷冷劃過耳膜。
『情緒,是魔的根源。』
『波動,只會使你墮落為獸。』
『你必須學會平靜,否則——』
原來是長老們要把她訓練成沒有情感的AI(喂
本來只是懷疑容安是不是亞斯伯格
Yian @yianc
1
第十一章 月照邀約前
十月的氣溫日漸轉涼,連交誼廳的火爐也開始提早點燃。從某個午後開始,霍格華茲的空氣裡就多了一絲古怪的躁動。走廊上的竊竊私語變多了,圖書館裡也出現不少鬼鬼祟祟在紙條上寫寫塗塗的學生。
容安原本不以為意,直到有天晚飯後,回寢室途中在樓梯轉角處聽見兩位雷文克勞女生在竊竊私語。
「我敢說他是在對我笑,」其中一位女生壓低聲音,「他還說『這顏色在某人身上不壞』——你說他到底在說我還是……?」
另一位女生翻了個白眼:「布萊克?他講這種話只是想看妳回去晚上睡不著覺罷了。他根本沒想過在說誰。」
那女孩不甘示弱,「他平常講完就走人,這次還特地回頭看了一眼——不可能只是湊巧吧?」
她們的聲音越來越遠,語氣依舊帶著難以掩飾的期待與小女孩式的自我安慰。
那晚回到寢室,瑪琪正一邊擦拭掃帚一邊對愛琳說話。
「……說真的,誰都知道波特今年還是只會邀莉莉——不過他再不出手的話,說不定別人就先下手了。」
「我倒比較好奇路平會不會又缺席,」愛琳一邊整理筆記,一邊若有所思地說,「去年他沒參加,今年也不太見他談論這些事。」
「但他其實挺紳士的吧?」瑪琪問。
「感覺是,至少行為舉止都很得體。」愛琳點點頭,「雖然總給人一點……距離感。」
「妳是說『神秘又溫柔的書卷型』那種距離感嗎?」瑪琪笑出聲,「我表妹說他就像老靈魂住進年輕人的身體。挺妙的。」
說到這裡,她忽然壓低聲音:「艾比·溫特好像還沒死心。她說前幾天在走廊上聽見布萊克誇一個六年級女生的眼睛——她堅信那是她自己。」
愛琳難得抬起頭:「但布萊克根本沒有直說人名吧?」
「當然沒有,」瑪琪攤手,「但妳也知道,只要一句眼神,她能寫出三頁情書」
「今年不知道他會看上誰。」愛琳皺起眉頭。
「誰知道呢?」瑪琪聳肩,「這種人啊,等他想動手時,從來不缺機會。」
說完,她的目光落到容安身上:「妳呢?妳會去萬聖節舞會嗎?」
忽然出現了舞會這個陌生的詞彙,容安愣了一下,慢了一拍才回答:「我不會跳舞。」
「不是問題啊,我可以教妳——」瑪琪一臉誠懇,隨即語氣一轉,「說真的,大概只有我們知道妳的條件,禮服一穿上……肯定是讓人眼睛一亮那種。」
她沒說完,只是笑得像在憋什麼內幕。
愛琳輕聲咳了一下。
「我沒嚇她啦!」瑪琪笑著說,「只是……萬聖節一年就這麼一次,我總覺得,哪怕只是穿得漂漂亮亮去吃頓飯,也值得期待一下嘛。」
容安沒說話,只是靜靜聽著。
最近無論走到哪裡,耳邊總能聽見關於舞會的討論。有人悄悄製作邀請卡,有人練舞步,有人則煩惱到底該不該主動開口。那種猶豫、期待、害怕又忍不住想靠近的情緒,像潮水一樣逐漸淹沒整座學校。
她靜靜觀察著這一切。
這些情緒對她來說既陌生又迷人。她不明白為什麼邀請與被邀請會變得如此重要,也無法想像,什麼樣的心情會讓人鼓起勇氣去牽起另一個人的手。
在她過去的生活中,沒有萬聖節舞會,也沒有那種可以隨意追求、放肆表達的自由。她曾經以為自己並不在意——她從未想過自己也會羨慕那樣的生活,但如今,好像有什麼不該有的渴望正在漸漸滋長。
霍格華茲大廳的天花板籠罩著淡淡的晨霧,映著灰白天光與燭火交錯的光影。十月的早晨帶著絲絲寒意,學生們正收拾餐具準備離席,交談聲此起彼落,直到一道熟悉又高調的嗓音劃破了喧鬧。
「伊凡小姐——!」
是波特。又是波特。
葛來分多桌的學生幾乎同時停下動作,下一秒,一束金色玫瑰從獅院長桌的方向悠悠漂浮而出,花瓣閃爍著細碎的亮光,宛如被灑了滿滿妖精粉,吸引了整個大廳的目光。
玫瑰穩穩停在葛來分多長桌中段,正好停在那頭紅髮女孩的面前。
「萬聖節將至,」詹姆·波特朝她行了一個夾雜戲謔的半鞠躬,語氣一本正經到近乎荒謬,「願否賞光,與我在萬聖夜共舞一曲?」
一陣騷動從學生席間竄起。
「有人計算過他被拒絕了幾次嗎?他連著幾年被拒絕了?」
「第二年了吧……還是第三?」
「他的毅力真的讓人很無言。」
莉莉·伊凡斯看著面前的玫瑰花,表情沒有絲毫波動。她緩緩抬起眼,淡淡地看著詹姆。
「不願意。」
語氣平穩,語速不疾不徐,清楚得宛如一記無形的咒語,把玫瑰從空中打回了現實。
有些人笑了出聲,有人吹了口哨,還有雷文克勞學生低聲說:「他果然又被拒絕了。」
但詹姆彷彿對這些反應早已習以為常。他聳聳肩,笑得無比灑脫,伸手將那束玫瑰收回來,夾在腋下,回身走回自己同伴那一頭,一邊還若無其事地拿起餐盤。
「我還是比較適合跟南瓜派約會,對吧,獸足?」
「你對甜食的忠誠遠勝女人,」天狼星懶洋洋地回。
莉莉低頭繼續喝著果汁,似乎毫不在意方才的場面。
那天之後,詹姆居然沒有再提起邀約的事。
沒有紙條、沒有巧遇、沒有在莉莉值勤時故意經過的腳步聲。
就這樣安安靜靜地——消失了。像一場只演了一半的戲。
莉莉依然故我地準時出席學生會會議、作為活動幹部安排舞會細節、斷然拒絕其他蠢蠢欲動的邀約者,表面看來毫無異樣。可只有她自己知道,那份預期中的煩人打擾突然缺席後,竟讓人產生一種說不清的失衡感。
圖書館的燭光在夜色中微微搖曳,書頁翻動的聲音與羽毛筆滑過紙面的細響交織成靜謐的樂章。
容安坐在靠窗的長桌旁,翻開的課本停在中頁,眼神卻飄向窗外,像是在思索,又像是在躲避什麼。
一個輕柔的腳步聲停在她對面,雷木思放下懷裡的書本,並未立刻打擾,只是略微偏頭看了她一眼。
「這時間妳常來嗎?」他的聲音輕柔,帶著一貫的克制。
容安回神,搖了搖頭:「偶爾。」
「這裡挺安靜的,」他輕聲說,坐了下來,「讓人忘記樓下還是一團亂。」
容安淡淡一笑,沒有接話。
雷木思翻開一本書,像是無意地說道:「今天有人在圖書館某排書架後練習舞步,被皮皮鬼扔了墨水瓶。我猜這段時間……這種事還會繼續發生。」
容安轉過頭看他一眼,語氣平淡:「舞會的事,好像大家都很在意。」
「嗯,」他沒有否認,「有些人把它當作一年裡最重要的事。也有人……只是想找個藉口,期待些什麼。」
「期待?」她似乎卡在這個字上,低聲重複了一次。
雷木思翻了頁,停頓一下才道:「妳不習慣嗎?期待一件事。」
她沒馬上回答,只是看著自己手指輕輕扣著桌緣,像在感覺某種說不清的情緒。
「以前我住的地方……不太鼓勵這種想法。」她終於說。
雷木思沒問是哪裡,只是輕聲回:「那樣的地方,大概不太快樂吧。」
「我不知道快樂是什麼樣子,」容安低聲道,「但他們說,太多情緒會讓人變得危險。」
「妳也這麼覺得嗎?」
她抬起頭,看著他。眼神仍是平靜的,卻比平時多了一層微妙的不確定。
「我以為我認同的。但最近……開始懷疑。」
他微微一笑,聲音像是春末的風:「懷疑,是開始的訊號。」
「你不覺得……那很愚蠢嗎?」她忽然問,語氣沒什麼起伏,卻像是第一次在別人面前試圖坦白,「大家為了一支舞、一句邀請,就那麼緊張、那麼在意……然後讓自己處在完全不穩定的情緒裡,為了什麼?」
雷木思想了想,才回答:「也許因為,那是一種證明。證明自己在某個人眼裡,是特別的。」
容安沉默了一會兒,低聲說:「我從沒想過這些。以前只覺得,那些起伏、那些激動,都很沒有必要。」
「可現在妳會想嗎?」
她沒有立刻回答。
良久,她才輕聲道:「我只是有點……羨慕。」
他抬起眼看著她,語氣很輕:「羨慕他們的自由?還是……那樣被在意的感覺?」
「我不知道,」她幾乎是呢喃著說出這句話,「可能是一種我沒經歷過的東西。但我開始想像,如果我能那樣活著……會不會不一樣。」
雷木思靜靜地望著她,眼中浮起一絲難以察覺的柔和與心疼。彷彿她說出的不只是話語,而是一段壓抑了太久的渴望。
「也許妳說得對,」他低聲說,「有些事……不試過,是不知道自己在錯過什麼的。」
他笑了一下,像是笑給她看,也像是對自己說。
兩人之間靜默了一會兒。圖書館的燈光靜靜落下,空氣裡只剩書頁翻動的細聲。
一段時間後,雷木思收拾好書本,與她點頭示意後先行離開。
那道背影在燈光下拉得修長而沉穩——帶著一種未說出口的猶疑,也帶著一絲將要鬆動的什麼。
圖書館只剩零星幾人,蠟燭燈芯被風吹得晃了幾下,燈影落在容安的書頁上,像是一小灘若隱若現的情緒。
她依然坐著,手指停在書角一動不動,眼神卻落在桌面某一點上。
如果真的有人邀請她呢?
她會是什麼反應?感激?開心?不知所措?
她想起瑪琪收到邀請時那幾乎要跳起來的模樣,想起餐廳角落一對對低聲交談的身影,還有那些女生用羽毛筆在日記上偷偷寫下的名字。
那種情緒,自己也會有嗎?
她有些懷疑。自己和她們不一樣。她從未被教導可以期待什麼,也不曾想過自己會成為某人的焦點。
再說,她在這裡……也不算真的認識什麼人,被人邀請這樣的事,大概也就是自己想想罷了。
她嘆了口氣,心想自己大概是被這種氛圍傳染了。
這種煩惱,也許從一開始就不存在。
就在她伸手準備合上書本的那一瞬,空氣中忽然劃過一絲動靜。
一張折成小方塊的紙條如同被施了定點飛行咒,自空中悄然滑下,準確無誤地落在她書本上——連角度都像是經過計算,毫不猶豫地停駐在她眼前。
她愣了一下,周圍沒有任何異常,圖書館仍是那樣半滿不空、安靜而日常。
那紙條無聲地躺在書頁之間,彷彿理所當然地屬於她。
她遲疑片刻,才小心展開它。
「我猜你還沒有舞伴。」
沒有署名,字跡俐落,筆觸偏向傲慢的從容——就像某人習慣在說話前先笑一下似的。
她盯著那行字,心裡升起一種奇異的感覺——說不出來是疑惑、訝異,還是某種……被喚起的意識。
她知道,這不是送錯的紙條。
這是寫給她的。只給她一個人的。
這是討論串底端!何不幫忙讓這串魔法煙綿延下去呢?